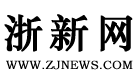墨色淋漓间,一匹劲健的骏马昂首奔跑,额间带着“白星”,鬃毛在风中飞扬,四蹄仿佛踏出风声……
这是徐悲鸿创作于1945年的国画作品《奔马图》,系徐悲鸿学生吕霞光的旧藏,于2009年经浙江省博物馆拨交给浙江美术馆,由后者珍藏至今。
徐悲鸿用他的笔,画出了一声穿越时空的嘶鸣,也成就了中国艺术史上重要的民族符号之一。
画骨也画神
1927年秋,上海黄浦江码头汽笛长鸣,一艘远洋客轮缓缓靠岸。下船的人群中,有一位年轻的画家——在欧洲留学8年后,徐悲鸿怀揣着“复兴中国绘画”的决心,回到风雨飘摇的祖国。
其实,早在1918年,23岁的徐悲鸿就提出过“中国画改良”的思路,认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而他选择表达的题材,便是马。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徐悲鸿之子徐庆平曾这样回忆父亲,“他认为马是世界上最高贵、最漂亮、最剽悍的动物”。
与历代画师为帝王绘制的那些“御马”不同,徐悲鸿笔下的马,雄强、骏健,连低头饮水时也自带一股悍气。
从浙江美术馆所藏的《奔马图》中,便能窥见徐悲鸿的独到匠心。马体结构严谨、肌理强健,体现出徐悲鸿对解剖学、透视、构图等写实技巧的精确把握;同时,水墨之间的笔势流动则继承了中国画写意的精神。
“徐悲鸿突破传统画马的程式,通过浓淡墨色对比,呈现明暗关系。”浙江美术馆馆长应金飞说,“马的眉弓、颧骨处墨色的皴染,是光影明暗的东方化表达;拉长的腿部与夸张的关节,既体现了解剖逻辑,又做了力量感的强化。”
徐悲鸿夫人廖静文曾透露,徐悲鸿画马往往从马尾起笔,大胆落墨,一气呵成。作画时,他不铺毡子,只垫旧报;不取现成墨汁,定要亲手研磨,只为追寻墨色里最细微的呼吸与韵律。
在中华美术史上,马是极具生命力的创作主题,留下了跨越千年的艺术回响。陕西霍去病墓的石刻《马踏匈奴》雄浑大气;甘肃出土的东汉铜奔马昂扬灵动;顾恺之《洛神赋图》中的马形神飘逸;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则尤重马的神态与个性……宋元以后,随着文人画兴起,鞍马题材创作愈发“尚意”,如宋代李公麟的《五马图》就是以“白描”技法捕捉马匹的内在神韵。
在应金飞看来,徐悲鸿画马时,既吸收了西方的技法,也复兴了中华艺术中的“写实”根脉。他让中国画的马,从书斋雅玩和宫廷苑囿中挣脱出来,重新接续汉唐以来雄强、充满生命张力的传统,并为之灌注了现代性的、关乎民族存亡的激昂精神,“徐悲鸿不仅画出了马的骨,也画出了马的神。”
迥立向苍苍
徐悲鸿所作国画彩墨浑成,尤以奔马享名于世。他早期画的马体态圆润、温顺可爱,而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危亡、山河破碎的历史语境中,他笔下的马也变得如李贺诗中的战马一样,“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
作家谢冰莹曾这样形容看到徐悲鸿画作时的感受:“令人一见,就像佩好枪弹,跨上马去,直冲入敌人的阵营,杀他个落花流水。”
悠悠报国之心,被徐悲鸿倾注到笔端。抗战时期,徐悲鸿笔下的“马”化作了民族的战鼓,创作于1937年的《迥立苍苍》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该作品借杜甫诗句“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为题记,以昂首战马隐喻家国忧思与抗争精神,笔墨酣畅淋漓、飒爽飘逸。
他还奔走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举办画展,将售画所得捐赠给抗战将士和难民。水墨骏马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有意思的是,除了在《九方皋》中的那匹有绳辔,徐悲鸿画的其他许多马,都是一无绳辔,二无鞍蹬,反映对自由美好生活的热爱。在他笔下,马不但熔铸进了艺术家自己的精神气质,也升华为一个民族的集体人格——坚韧、奋进。
他的奔马始终与“自强不息”相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接下来的篇章如何续写,取决于我们如何奔跑接力——既不忘来路的风骨,又能踏响属于这个时代的坚实蹄音。这份追问,或许就是我们在欣赏徐悲鸿画作时,内心真实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