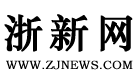柯兰
一支细水,从钱塘江源头流出,在开化县境内一路汇聚,逶迤间揽住一方水土。烟雨朦胧中,马金溪畔的下淤村,背靠青山款款而立,犹如一位青葱少年,羞涩中透出一份坚毅,朴实中深藏着文化的清流。冒着雨,我与一群文学爱好者走进这个江南版的“文学的村庄”,向往一场心灵的碰撞。
下淤的文化清流源自马金溪畔的包山书院,南宋中期著名儒家学派婺学创始人吕祖谦曾在这里讲学,历史上著名的“包山之会”更是让马金溪上儒风浩荡。回望南宋淳熙二年(1175),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出面邀请陆氏兄弟与朱熹见面。于是,“鹅湖之会”在江西上饶鹅湖寺上演。没想到,“鹅湖之会”持续三天,最终双方不欢而散。南宋淳熙三年(1176),也就是鹅湖之会的第二年,吕祖谦再约朱熹和陆九渊到他讲学的包山书院见面。“东南三贤”朱熹、吕祖谦、张栻,加上远道而来的陆九渊如约相聚,四位大咖,均是当世学富五车的赫赫巨子,加上其他儒林名士,在包山书院一起再论儒学文化。那是个落雨的暮春三月天,大儒们在此谈经论道,逗留九日。不同于“鹅湖之会”的剑拔弩张,“包山之会”则显得其乐融融,还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精彩诗篇。人们至今仍在回味那堪称世界一流的大师们云集马金溪畔的包山,联床听雨、赋诗唱和的文化大餐。
如今,“包山之会”形成的文化清流通过马金溪已经传递到下淤村。村里前几年在大力发展乡村文旅产业的同时,别具一格地与20余位来自大城市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签订驻村协议,持续植入高品质的文化艺术品牌内涵,在原乡人、归乡人、新乡人之间形成良性互动,进一步激活乡村文化产业发展。
走进村里,水岸烧烤、金溪游船、滨水乐园、邻水民宿等溪边特色旅游设施,在我们眼前一一晃过;梨花公社、霞洲艺术村、汪瑶艺术馆、钱江源乡村艺术馆等艺创花街的高雅艺术场所,让我们纷纷驻足细品。还有修旧如旧的一幢幢民房,门口挂着各种名目的工作室,从造型和摆设中隐隐透出不同特色的艺术光华。
听说著名长篇小说作家于卓在村里的艺创空间驻村体验生活,并专门成立了个人工作室,我们慕名前往参观。于卓,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多部长篇小说获国内大奖。走进于卓书香四溢的个人书屋,墙上的画,是他亲笔“涂鸦”;桌上的书,是他个人的文学成果。当然,也有开化当地作家的长篇小说。与于卓同时驻村体验生活的,还有著名诗人赵丽华,她的文学“花粉”同样在这里传播。当我们正想从这里探寻一位位文学大咖的成功之道时,一阵爽朗的笑声从身后传来,有人悄声提醒,“于卓老师来了。”
我们见面,握手,座谈交流,谈笑间感受着浓浓的文学氛围和乡土元素。这几年,作家于卓在这里几乎已经化身为村民于卓,每天俯下身子、卷起裤腿,沿马金溪行走,与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对话,与纷至沓来的一批批游客交流,将沾满泥土的脚印留在村庄的每一个角落,与这里的土地、空气、建筑产生种种神秘的关联,像是融合了血脉一样,这片土地属于他,是他的第二故乡。很多时候,于卓还会与开化本土作家开展关于乡土文学的种种讨论,这样的讨论往往会碰出丰富多彩的思想火花。
花木扶苏,草叶清亮,作家们一颗颗纷繁躁动的文学创作之心,在“文学的村庄”得到了轻柔的安抚。我不知不觉间联想起著名作家周立波曾经说过的话:“文学的园土是在人民生活里。作家必须长期扎根在生活的肥土里边,才会有出息。”上世纪50年代,周立波为反映波澜壮阔的山乡巨变,回到故乡湖南省益阳市清溪村深入生活。清溪村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写出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更是一炮打响。如今的清溪村,不仅仅是《山乡巨变》背景下的生产建设“山乡”,更是将文学精神融入村庄建设的“新山乡”。慕名而来的外地人漫步清溪村,仔细寻找60多年前《山乡巨变》所徐徐展开的壮美画卷,感受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全新面貌。清溪村也由此成为全国人人向往的“文学的村庄”。
作为江南版的“文学的村庄”,下淤村不但是大城市文学大咖的精神家园,同样也是本土作家的精神家园。听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开化县作协主席孙红旗就是这里的常客,也几乎成为这里的村民。他撰写、出版、发表的10部长篇小说、100部中篇小说,里面包含着无数钱江源头的开化元素,下淤元素也频频亮相其中。这几年,开化县还有16位本土作家陆续发表长篇小说,打造出的“长篇小说开化现象”在浙江文坛彰显,就如同马金溪畔曾经发生过的那场久负盛名的“包山之会”。
孙主席带着我们在村中漫步。入村如入画,不管是生态连廊,还是高端民宿,或是散布在田野村落里的小景观,人们随时都能与一句句沁人心脾的诗句照面,与一个个启迪人心的哲思相遇。这些文学的“活态化”样本,共同构成了下淤的文学地标。和谐大美的“文学的村庄”,文学的隽永与溪流、稻田、民居构成声色交融的艺术体,自然之美变得深邃。俯拾皆是的文学元素,如同星星点点的微光,照亮了村庄充满生机的现在与未来,它们是游客们乐于享受的精神文化休闲场所,更是他们探索以文化力量赋能乡村振兴的“样板田”。
当严肃文学在茫茫人海里“寻找亲人”,当快节奏的生活挤压着人们的阅读时间,下淤村,却在文学和村庄间构建出亮丽的人文风景。在这个“文学的村庄”里,我找到了文学更多活跃的空间——文学就在田边和地头,就在花草摇曳处,就在百鸟飞翔中,就在风水绝佳地,更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
来源:衢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