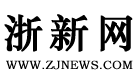庄月江
2023年10月2日,癸卯八月十八日,晴。三点多起来,改、补《集外之余》信函题,并加入平平2006年的一封电邮。弄好后即发给印刷厂小温。
又想到带几枚图章给骑塘桥(作者故乡)。找出王耀志刻并赠的文仙(作者妻子)与我的名章,以及他刻赠我的劳碌斋印与生肖虎印,还有1974年浙江少儿出版社编辑范成璋刻赠我的两头印“庄月江印“与“月江藏书”。
与范成璋认得也是缘分。那年,衢化总厂政工组介绍范成璋与萧新桥到铝厂采访我。1972年12月24期《工农兵画报》刊登了以我的短篇小说《苹果树下》改编的11幅连环画。出这本刊物的浙江人民出版社派范成璋(江苏人,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与萧新桥(天津人,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从事古文研究)来采访。那时,周文仙携雨虹、雪虹刚迁到上祝不久,我家租住在上祝村大路园溪边知识青年住过的“十间头”简陋小屋中,不到20平方米。
我当时是出铝工,长期上小夜班(午后4点到半夜12点),他俩上午由铝厂办公室人员带到我家里(从厂部沿溪而行,不用十分钟)。他们好像是来了解“评法批儒”情况的。聊着聊着,对我说的“我看报纸上刊登《论语》章句供批判,倒是古文经典的大普及”这句话,他俩有同感。于是,就偏离主题瞎聊了。1952年至1958年我在杭州读了六年中学,住校,贪玩,喜读课外书,了解杭州风景名胜,于是他俩的“采访”变成了三个人的瞎聊。我留他俩在我家吃便饭。
范成璋的妻子(萧山人)也是农村户口,他与我惺惺相惜,后来刻了这枚“两头章”寄赠我,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枚朋友刻赠的印章。此后,我们一直互通书信。浙江少儿出版社出了新的连环画,他都寄来给我的两个孩子。有一年去杭州,我与妻子到浙江少儿出版社看他,他妻子还杀了只自家养的鸡招待我们。
范成璋喜欢集邮。
我读小学五年级时就喜欢集邮,自己用硬纸板和玻璃纸做嵌邮票的小本子。家里杂物堆里有一些旧信,我就将信封上有孙中山像的中华民国邮票,以及盖着“代邮”小字的大清盘龙邮票揭下来(信封年代久远,邮票很好揭下),嵌在邮票本上两厘米宽的玻璃纸后面。
1952年,我考进杭州树范中学。同班有几个同学也喜欢集邮,而且学校大门斜对面有一家集邮店,店里有纪念邮票(盖销票)出售,顾客有纪念邮票还可以同店里交换。
那时候集邮,搜集的、买来的、与同学交换的,都是盖销票。集邮,在于“集”。“集”才有兴趣,乐在其中。不知为什么,渐渐地,集邮变成了“买邮”,也许是邮政总局发现了其中的商机。大概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某一年,邮局印制“年册”销售,居然门庭若市。到后来,还须“预订”,即今年订明年的,先付钱。渐渐地,很少有人用纪念邮票寄信了,贴在信封上的全是普票,几乎看不见纪念邮票了。这也算中国特色吧。
1958年12月14日离开海宁斜桥到衢化工作后,我读书时的这两本自制邮册,一直放在老家楼上西房的三斗桌抽屉里,几年后不见了。那几年,父亲在合作商店鸟船埭的“下伸店”工作,每天早出晚归;母亲患精神病,几乎整天站在元吉弄口,家里“门虽设而常开”……后来有人相告,我的十多只蟋蟀盆,以及楼上抽屉里的邮票册,都是西市梢一个“寄亲”(父亲曾经的同事,互相认亲,“干亲”之类)的儿子拿走的。这是我的第一次集邮。
第二次集邮,集的也是从信封上揭下来的盖销票。其实也无所谓“集”,搜集起来放在一起罢了,大约好几十枚,后来都寄给了爱集邮的范成璋了。
第三次集邮,雪虹读小学高年级后喜欢旧邮票,零零星星搜集了一些。1979年我调入衢化宣传部后,老友沈友润、刘德威,以及沈尔坤等都喜欢集邮。上世纪80年代初,衢化还成立了集邮协会。那时候,有些纪念邮票的小型张,一般人舍不得买。1984年冬,《衢化报》采编人员到金华参加职称考试期间,参加工作不久的梁锋花32元买了一张四方联猴票,大家都不理解。
买整本的年册,我是从1985年调到《衢州报》才开始的。报社租在天宁巷民居。天宁巷接南街,对面就是邮局。邮局的吴斌、段小红是报纸的通讯员,鼓动我买年册,说集邮不用花心思,他们可帮我购买。这便是我购邮册的开始。
随着年岁的增加,老了,什么都觉得无所谓了。与妻子商量,去年开始不再预订邮册了,本来每年订两册。上半年清理一下,将一份完整的,共有几十本,给了雪虹。雨虹自己买了好多年,让她补缺。如是,剩下三十多册,给桂芬十册,另三个表弟与两个表妹各二册,云江一册。还多十余册,偶送友人,已送出八册。
十一二岁开始的集邮,终于在86岁时愉快地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来源:衢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