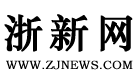庄月江
在《自我和谐——生活是本没有句号的书》自序中,作者周耕妥介绍了自己读书与写书的经历与感悟,写道:“不管你是谁,只要与书为伴,与书为友,以书为师,将不仅乐在其中,而且乐在知识外化的气质之中……”
周耕妥是原衢县乌溪江区洋口乡文化员,1986年调入衢县县委宣传部,1991年调入《衢州日报》当记者。1999年1月,他入职省十里丰监狱当狱警,不久被选调到省监狱工作研究所,从事监狱理论研究与《浙江监狱》期刊编辑工作。
新闻工作的实践和修炼,周耕妥养成了“顺则凡,逆则仙”的思维方式和习惯,能把自己对生活、对工作、对社会的感受,用理论化的语言说出来,多篇论文、文章发表在大刊,并屡屡获奖。在“爬格子是门入静入定的娱乐艺术”的觉悟和修炼中,周耕妥或参与策划、或主编、或撰稿的著作有十多种,另有多个课题获奖。
《自我和谐——生活是本没有句号的书》全书八章,由49篇文章组成,皆充满生活哲理。简言之,作者通过读书和写书来诠释做一个好人的道理。
对于一个人的流芳百世与遗臭万年,作者这样阐述,“自古以来,可惜可叹可哭可恨的是,有许多的官员和大款明明有流芳千古的能力和机会,却偏偏要违法乱纪,不仁不义,争取遗臭万年。殊不知,为好人易,为恶人难;说实话易,说谎话难。为恶人须大费心机,说谎话须大打草稿。一旦做了官,或成了大款,总之成了名人,就有了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的资格和机会。”作者详尽地举了杭州岳庙里忠贯日月的岳飞,以及跪在岳坟的秦桧的例子。(P.048)
周耕妥认为,生活,常态是柴米油盐、安居乐业;境界,是以善良和爱心对待他人甚至其他生物的向善影响而营造的和谐环境。人们要进入这个“环境”之门,需要信仰和道德引领才能找到钥匙,需要文化和智慧的驱动才能引领“双脚”步入其中。而一个人的文化与智慧,源于读书。因此,多读书、读好书,可以把“各种蠢事,在每天阅读好书的影响下,仿佛烤在火上一样,渐渐熔化”(托尔斯泰语)。但是,“知识没有善恶之分与美丑之别,在有仁爱精神者手里将会开拓和深化善行,在不同信仰精神者手里,或为善行助力,或为邪恶开道,在极端理性主义者手里,将是追求金钱财物的工具,专司己利的技巧”。(P.157)
作者在《真善美是职业生涯的灵魂密码》这一章中,提出了“监狱工作的真善美”观点。作者认为,监狱是“道”,是以暴制暴之道,是因果报应之道,是改邪归正之道。这道,就是在罪犯脑中植入“守法意识”,在罪犯心中导入“健康心理”,在罪犯手中传授“生活技能”,在罪犯体内培育“免疫力”。并从监狱工作的目标层次、宽严相济的坐标构架、罪犯修心教育、劳动改造意义等不同角度进行阐述,得出“监狱工作的‘成果’是法定的把罪犯改造成守法公民的目标的实现”的结论,令人信服。作者又从实践中总结出:“安全稳定是‘真’,教育改造是‘善’,刑释人员持续做守法公民是‘美’。”
“善”与“美”好理解。对于真,看了作者的解释,就清楚了:“‘真’在监狱民警的职业信念上、工作理念上、岗位责任上、具体行动上。”(P.254)而对于罪犯改造,作者在《罪犯改造好从人性上说只是阶段性的好》中阐述:“罪犯是可以改造好的。永久性的好是应然目标,阶段性的‘好’是必然要求……这个阶段性改造好的效果,也许会延伸到社会、持续到将来,甚至成为永久性的改造好。”这里又提出了一个社会需要关注、关心刑释人员的问题。
作为读者,我特别重视本书中的短文《为人处世要有“不动点”》。作者在此文中提出:“不动点是超越权力权利、金钱财富、情感取向的铁律。即自然与社会状态中具有同一、永恒、终极、不变性质的不证自明的公理、定律,以及终极抽象的概念、规律等。”我想,这为人处世的“不动点”(铁律),就是做人的规矩和底线,也就是古人说的“仁义礼智信”和“礼义廉耻”。
在这篇短文中,作者还举了三个多年前曾经成为司法热点、大多读者耳熟能详的事例:一个成年男子在KTV酒后性侵同行女子,女子受伤流血后仍不罢手,男子遭众人殴打,逃跑时摔死。男子的父母将打他的人告上法庭,索赔130多万元;一个60岁老人在公园的树上偷摘杨梅时,枝丫断裂掉下摔死,亲属向景区索赔60万元……作者感叹:“本来这三个案例中的死者已经很丢人了,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三个死者的家人还能理直气壮地找别人要钱,这是典型的为人处世没有‘不动点’,值得深思。”
2015年,周耕妥的专著《治狱不动点》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副所长、《犯罪与改造研究》杂志主编高文先生为此书作序。在此引用几句,以让读者了解周耕妥的为人:“耕妥同志最初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不太会说话,但接触深了,我发现他原来是一位钟爱监狱理论研究工作,勤于思考,卓识远见的同志。《浙江监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监狱理论研究期刊,其中耕妥同志所编辑的文章,鲜明独特的观点总是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编辑选用稿件的方向代表的就是监狱理论研究的方向,监狱工作实践中出现的难点、热点问题,往往是由编辑的眼光最早捕捉到,进而组织深入研究的。”
本书尾末,还收录了作者上世纪90年代在《衢州日报》工作时,为《衢县县志》写的文史资料《天脚寺剿匪记》《红军桥》《乌溪江水心中流》,读来分外亲切。因为文章中写到了洋口、白岩、藤桥、上高输、下高输、柴家、岭头、举村这些我多次去过的地方,如历其境。
我第一次到乌溪江,是1986年5月15日。我与文字记者缪宏、摄影记者陈康,到乌溪江区最偏远的洋口乡采访并调查政府扶贫情况。先车后船,当天傍晚才到达洋口乡政府驻地。经缪宏介绍,我认得了周耕妥,他是乡里的文化员,一个说话不多挺朴实的小伙子。那时候库区贫困,我们在乡政府食堂吃饭,最好的菜是周耕妥从溪沟里捉来的小鱼,至今记忆犹深。
来源:衢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