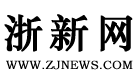陈于晓
在江山市,碗窑,碗窑,这样吟诵上数遍,似乎碗窑就变成了一曲“婉转的童谣”。并且,我由童年记忆中夏夜那一闪一闪的萤火虫,想到了碗窑的窑火。这些窑火,当然是熊熊的,点燃在这一方水土的光阴深处。
据说,碗窑这一地名的由来,就是因为北宋时期在此地建了碗窑。明代福建布政使班琴曾来此扩建有100座窑厂。从北宋开始到明清,前后历经800多年,此地所制青花瓷,曾销到浙闽一带,乃至海外。
如今窑火已冷。窑火真的冷了么?我相信,在宋代碗窑的遗址群中,依然可以触摸到窑火的温度,那是一种岁月所沉淀下的温度。倘若你用心去感知,这种温度,始终是在的。如同你只要用心去听,你依然能听见某一只青瓷器在时空深处,说着清脆悦耳的话语。
也许,所有往昔的光与影,都不曾弄丢,大地都会以某一种方式保存着,而你在很多年以后,依然可以走进它们,只要你找到了某一条秘径。如今,取一些碗窑的泥土,还可以烧制出那精美的青花瓷么?这样想着时,我抬头望了望碗窑的天空,是的,我希望着,能在碗窑天空的云破处,寻找到那一抹“青”。
那等着某一场烟雨的天青色,终究已经沉浸在往事里了。沉浸在往事里的这方叫碗窑的水土,沧桑而厚重。资料上说,碗窑承载着商代、西周、春秋、隋朝、宋朝等五朝的文化遗迹。古老文明的光,在记忆的潮湿处,闪闪烁烁。此刻,吹拂着我的,是来自旧年的湿漉漉的风么?我仿佛听到青铜编钟的乐声了。1967年,在这方水土中,出土了6件春秋时代的青铜编钟。也许,在“薄如纸,颜如玉,明如镜,声如磬”的青花瓷中,也会浸润着编钟的色泽与声响。抑或,你可以在一只青花瓷的某一处,领悟到些许青铜编钟的神韵。
只是,我所听见的钟声,可能是千年古刹石壁寺的钟声。真的是钟声么?如此缥缈,很像不是真的,许是一种幻听。这又是哪一年的钟声呢?石壁寺还是从前的古寺么?星移,斗转,当这一炷香火被点燃之后,那些曾经的香火,都去了哪儿?花落花开,起居在古寺内的,是佛像,还是佛?
而当石壁寺的香火入了深渡祠堂,就是烟火了。在一切都静默下来的时候,还会有旧年的身影,在祠堂的深处,轻轻地晃动么?这些上了年岁的砖瓦,总像是铺着一层或浓或淡的霜,斑驳着,这是时间所留下的印记。每每看见烟火,我的心头总会一暖,人生代代,就延续在这烟火的生生不息之中。
从一碗窑火中,走来的碗窑人家,就宁静在一碗烟火中。我喜欢“宁静”这个词,也许就是这“宁静”,洇开了一曲碗窑的牧歌。日出时分,下地去,耕牛在前,农人在后,耕牛是被农人赶着的;等到日落时分,回家,农人在前,耕牛在后,耕牛是被农人牵着的。但在我看见的一幅有关碗窑的画图中,走在溪坝上的耕牛和农人,若即若离,戴着斗笠的农人,披着浅浅的烟雨。我分不清,画中的耕牛和农人,是在出发的路上,还是在归家的途中?那清澈见底的溪水中,只留着明晃晃的倒影,却没有写上我想要的答案。
云雾里,碗窑是一幅水墨,当云雾散尽之后,碗窑会是一卷油画么?
散布在草木深处和浅处的农家乐,那白墙,那黛瓦,像一枚枚静谧,轻轻地依着山,静静地傍着水。我歇脚的时候,草木似乎在走动着,将木屋遮了又遮,但终究没能遮住,只需换个角度,木屋又暴露出来了。那些婀娜的藤蔓,也许是可以攀上竹楼去跳个舞的,倘若由此唤醒了竹的记忆,我以为已搭建成竹楼的竹,仍会再次摇身成挺拔的修竹。如此,在竹楼中吟唱的人儿,又可以徜徉在悠悠的竹海中了。
杨梅、西瓜、树莓、猕猴桃、茶油、蜂蜜……以及各样的新鲜蔬菜,都是碗窑的特产,可以在农家乐中慢慢品尝。是的,必须“慢慢”,在碗窑,时间自然是慢的,就连日头,过老半天了,还停留在老地方。品一杯清茶时,可把山听空。心远了,淡淡的茶雾,也可以飘得很远,或者,茶雾会在某一片山崖上,挂成瀑布。然后,渐渐明白,山的空与不空,不过是我的一种心境罢了。
碗窑是山,碗窑是水,碗窑是一个地名,碗窑是一个绿水青山的故事。沉浸在碗窑的山水之中,是适宜翻一卷诗书的,最好是有着青花瓷插图的那一本。这样,你就可以让自己走到字里行间去,或者还能在碗窑的往事中,逢着旧年的窑匠。当你和制窑人一起,点燃一把窑火时,不妨将你所采撷的碗窑的翠绿,也搬入到窑火中,如此,借恰好的火候,就可以出炉一窑“青”了。
作者简介
陈于晓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作品散见《诗刊》《星星》《诗潮》《星火》《草堂》《诗歌月刊》《长江文艺》等,多篇作品入选年度选本,著有《路过》《与一棵老树的对话》等。
来源:衢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