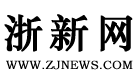郑凌红
在某个夜深的神经末梢,新鲜的书跳出来,新奇的感觉跳出来。浪漫不在烟火人间,而在《声音之茧》。这本书,成了我某种意义上的第一,唯一。尽管,对于“天籁之音”的立体真身,我只是百闻,却未一见。
时间是每一个写作者的风帆,在每一个熟悉或陌生的瞬间,有心之人,有缘之人,都能感受到写作者对于时间的态度。这态度如同信仰,不舍昼夜。我以为,《声音之茧》是一本时间的书,作者七年之痒终成此作,想来其间点滴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一本书,都是自己人生的记录本。《声音之茧》延续了作者大气、空旷、哲思的写作风格。她和大地私语,她和时间拥抱,她用追光赶影的态度,一字一字写下人世间的片片诗意。大起笔从四季落下,《春声》《夏籁》《秋吟》《冬乐》,往里看是对应的四季,十二个月,一季,六个节气。她虔诚地跟着古人的足迹,沿着历史的脉络,顺着光阴的大道,铺开了人间一场场浩大的花事。
所有的共情,都来自于人生的阅历、自我的觉醒、心中的大爱。作者在自序中说道:雨落在这件唯美的声音雕塑上,山林中便会想起一场独一无二的雨滴交响曲。这在我看来,这就是作者的文字之美、语言之力、心灵之感。
《声音之茧》以梦为马,从立春启程,从故乡玉环的回望中款款而来。母亲在缝纫机前做新衣,苏老师带来一枝桃花,萤火虫般焦虑迷茫的家长和孩子,袅娜的越剧唱段,秋天的第一批黑脸琵鹭,辛丑年惊蛰的敲梆声,金鸡岭半山腰的那一眼山泉,像黑沙滩一样老去的姨婆,双手紧捂胸腹走下轮船码头的长人苏,娘家桂花树下母亲的黑痣——这是春的交响乐,彼时无声似有声。这样的气味,我以为,是亲情的气味,这是苏沧桑的春之声。
这些年,我看苏沧桑的文字,愈发地感受到文字之外的禅意,而她的文字是缓慢的、轻柔的,刚强的质地不易被人察觉,却透着历经千山万水的从容。散文写作,从理论上说具有先锋色彩。将所有的文字用“人”的一道道轨迹串联起来,这是写作高手的功力,也是一个人对生活最深刻的思考。《立夏·伞》《立夏·白色痛》以对话的脉络,揭示了过往的痛和前行的苦。我在文字里看到作为一个“人”的脆弱和关于我们与这个世界如何相处的某种思考。这样的铺展覆盖了整个关于夏天的点点滴滴。
秋和冬,我愿意把它们合在一起。它们或许是我眼中认为的最靠近万物的另一番解读。我惊讶于作者的细腻,对她的童年有了好奇。她说:我七岁那年立秋,一个人跟着姨婆到她家小住。我喜欢桃树和文旦树,喜欢她屋后的小松鼠,喜欢上山捡柴,喜欢她给我炒的小葱土豆,可是那里什么都好,就是没有人,没有人!有风吹竹叶的哗哗声,有暗夜的虫鸣声,就是没有别的人声……
这些年,我开始对心理学进行较为系统的关注,发现一个作家的童年与他的作品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为什么,有的作家作品深沉,有的作家作品空旷,有的作家作品含蓄,它的源头之水在于童年的经历,以及童年时期对这个世界的印象。当然,这或许有差池,但我深信不疑的是,每个人的人生际遇都会像一杯回味绵长的老酒,对着好菜下了肚,顿觉红尘攘攘,神清气闲,梦稳心安。作者的步伐稳健而诗意地漫步在苍穹之下,在威尼斯,在马尔代夫,在泸沽湖,在东海边温州龙港余家慕村,在九月的焉支山下,在明月山北,在阿坝壤塘觉囊非遗传习所,这些是秋天的吟唱。而冬天对应的更多的是那些特别的人,有紧密关联度的人,有反射弧的人,他们和作者的焦急碰撞出了生活的哲思。作者在时间和文章的布局上用心良苦,一方面是行旅的梳理,另一方面似乎是心迹的极致对应。
我把目光停留在《大寒·梦湖》,这是旅程的终点站,也是旅程的始发站。我看到一个灵魂有香气的女子,在苍穹之下回望自己走过的路,看过的人,想起的事,一切都放不下,一切又飘然向远,似梦非梦,它是贝加尔湖的耳朵,也是众生的耳朵。
来源:舟山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