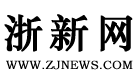中学毕业,我进了县城的国营化肥厂。
说是县城,因是化工企业,其实是离县城三五里的山坳,两排三层厂宿舍,厂里把上同一轮班的职工安排住在同一层,以便作息。
几乎是清一色的年轻人,20岁左右。每个房间住3个人,三张木板床,一张抽屉桌,以及脸盆、毛巾什么的。我还有一个物品——一个人造革的拉链袋。由于是刚开始职业生活,还有点“水土不服”和“赖家”,一到休息天就往乡下家里跑,所以袋子里放置的东西并不多,只是一些换洗的内衣,塞在床下,瘪瘪的。
20世纪70年代末,这样的身份并不低微,这样的生活也不寒酸,反而很骄傲,很风光。
但住久了,堆放的物品也在增多,比如书、杂志,这个时候,我便想要添置一件“家具”,比如一个纸箱。
我想到了同轮班但不在同一个车间叫林力的高个子工友。他是城关人,听他说过,他的父亲是在文具店上班的。文具进货应该用纸箱包装着,卖了文具,纸箱不就空出来了吗?这正如我小时候知道的,卫生院里的针剂打完了,这装针剂的盒子就空出来了,有关系的人就可以拿来当文具盒使用。
我与林力说,你叫父亲拿一个纸箱送给我吧。他应允着:好的好的。
于是,我开始期待。但每次看到他骑着自行车来上班,车后架都没有纸箱,我不免有点失望。下班后我们一同从厂门口出来,或者碰到他从宿舍扛着自行车下来时(城关人上夜班,也可住厂宿舍),我总是又提醒他,给我带一个纸箱哦,别忘记了。他说,知道知道。
我不认识他的父亲,但我开始惦念他的父亲了,而且知道他父亲上班的文具店的位置,那个时候都是公家开的店,全县城就一个文具店,而且就在我们看电影的县大会堂前的街道上。
每次白天去看电影,或者晚上赶早去买电影票(夜晚店关了),走过文具店门口时,我都要扭过头张望。文具店里有点灰暗,我猜想,这个瘦瘦的店员就是林力的父亲吧。我甚至想象着,有一个纸箱里的文具正逐步搬出来卖了,这个纸箱空出来了……我太需要一个纸箱了,那清清爽爽的纸板构成的一个空间,能用来放置物件,而且纸箱本身就是一份响当当的“资产”。
每一次失望地看着林力骑着空着后架的自行车来上班,每一次下班还是叮嘱他带一个纸箱来送我;又一次落空,又开始新的期待……他嘴里应承着,但低头就走,似乎他推说过理由:没有纸箱,或者店里不让带了……直到轮班调整,我们不在同一个轮班上班了,我才断了这份念想。
去年,我新购的房子装修,可以称得上是一套大房子了,不断运来的材料、家具、电器,拆出的纸箱,不时扔满房间。这些会有人来收购的,但对于这些易燃物,出于安全,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尽快移走,于是,有时候对送货的人说,你把这些纸箱折叠打包运走吧;有时候就叫上小区保洁工:搬走,搬走,送你好了,不要钱。
这些大小不一的纸箱,一次次堆满我的房间,在经历那一次性的使用后,就不再是纸箱,变成废物或者是回收材料。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多年前那只未拿到手的纸箱。李剑峰
来源:台州晚报